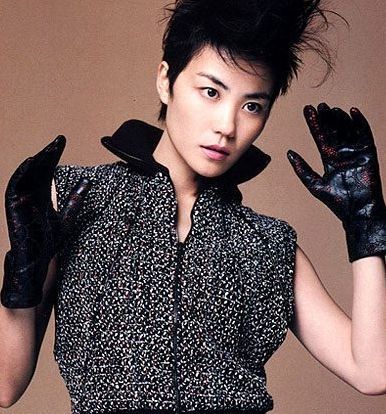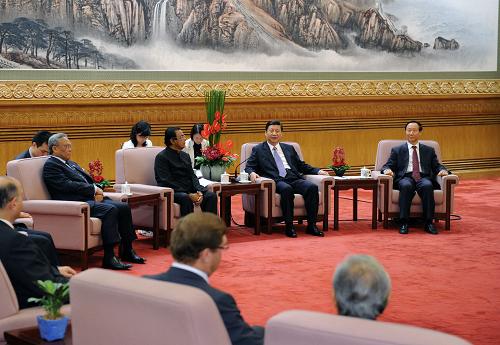从人性的捕捉者,到时局的揭露者,再到政治的追随者,曾洋溢在曹禺笔端的灵性,慢慢干涸了。
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
2010年9月24日,曹禺诞辰100周年。
曹禺生前所在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幼年生活过的天津,故乡湖北潜江,乃至更多的地方,都在以不同的方式,准备纪念这位杰出的戏剧大师。
很多人将聚集在一起,描绘自己心中的曹禺。也许在他们当中,有人会提起曹禺晚年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。
八十年代初,著名画家黄永玉曾给曹禺寄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,他说道:“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,所以我对你要严!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,一个都不喜欢,你心不在戏里,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,你为势位所误!”曹禺看后非但不生气,反而恭恭敬敬地将这封信专门裱成一册。后来,他还让英若诚将此信念给前来造访的美国剧作家阿瑟·米勒听。
纵观曹禺一生,不难发现,从23岁到33岁,曹禺用十年时间写完了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等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。随后的人生中,无论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,都不能再与从前同日而语。大起大落的创作生涯,留给人们的是费解的“曹禺现象”。
曹禺胸中那块“通灵宝玉”是怎么破碎的?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,这仍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。
转型
1934年7月,曹禺的成名作《雷雨》发表在巴金主编的《文学季刊》上。1936年,第二部作品《日出》登上了《文季月刊》。两部作品的横空出世,引起了话剧界的极大震动,导演欧阳予倩把曹禺称作“剧坛忽然跳出来的天才者”。
1936年,应校长余上沅的邀请,曹禺受聘为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,后担任教务主任。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国话剧艺术的最高学府。
很快,曹禺成了国立剧专的一块“金字招牌”。不仅大批学生慕其名而报考该校,他的课也成为了学校的一大“景观”。据当时就读于剧专的吕恩回忆,曹禺的剧本选读课最受欢迎,因为在课堂上曹禺常声情并茂地用角色的声音朗读原文,一会儿扮作罗密欧,一会儿扮作朱丽叶,引得学生们如醉如痴,忘了下课。四十分钟的一节课经常两节连堂。“别的班听见曹禺在哪个班上讲课,只要没课都过来听,教室里头坐满了,窗户台坐满了,走廊里坐满了,都来听他的课。”
那时的曹禺,还不满30岁。
对于突如其来的名声和外界冠给他的种种称号,曹禺自己都有些猝不及防。他晚年回忆,“那种无度的捧,无休止的捧,我也被捧烦了。”
果然,在1942年改编完《家》后,他便感到难以自我超越了。“再像《雷雨》、《北京人》这样的路子,这样的一些题材写下去,我自己觉得都不行了,写不出新意来了。”
于是,他将目光转移到了历史剧上——从1941年到1943年初,郭沫若已经发表了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、《高渐离》等六部抗战历史剧,话剧界正刮起一股强劲的历史风潮。“当时我想写历史剧,也可以说受到郭老的影响。”曹禺回忆道。
但曹禺的转型尝试以夭折告终。出道以来一路狂飙突进的势头,从此一去不返。
晚年谈起这段经历,曹禺感叹地说道“我们常犯的毛病,不是缺乏历史资料,而是缺乏飞扬的想象力。太拘泥于史实,太拘泥于一些框框了”。
其实,令曹禺“拘泥”的远不止这些。
误读
1935年4月,《雷雨》在日本东京公演。这是《雷雨》诞生以来第一次具有广泛影响的演出。由于原剧本太长,剧团删去了“序幕”和“尾声”,并且在落幕前安排工人代表鲁大海出场,原因是“鲁大海是暗示新兴的人物,作者不应使他‘不知所终’”。
对此,曹禺旋即去信。他写道“我写的是一首诗,一首叙事诗……但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”。他希望观众不要“问个究竟”,而是把它“当一个故事看”。
在1936年1月写下的《雷雨·序》中,曹禺进一步解释道:“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、讽刺或攻击些什么。”“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,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。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,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。”
曹禺要描绘的,是超越阶级立场和社会问题的“人性”。
但是,众多误读的包围下,他的声音显得微乎其微。
1935年10月,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新新影剧院公演《雷雨》,次年又相继在天津、上海等地公演,“卖座之盛,前不多见,甚至超过电影。”到1936年底,全国各地上演《雷雨》已达五六百场。接踵而来的各类评论,几乎无一例外地探讨起了《雷雨》中暴露的“社会问题”,比如婚姻问题、家庭问题。
1936年6月,左翼文学阵营领袖人物田汉更发表评论,指出曹禺虽然“也接触了好一些社会问题,如大家庭的罪恶问题,青年男女的性道德问题,劳资问题之类”,但这些问题只是源于“不可抗的命运”,“这样灰暗的、神秘的看法,对于青年的力量这样的估计,可以回答中国观众当前的要求么?”田汉尤其对剧中鲁大海被其他工人代表出卖的情节不满,认为曹禺“留给我们的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辱骂和污蔑”。
这些,与《雷雨》的初衷相距甚远。
随后,1937年2月上演的《日出》也遭遇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命运。又一次,《日出》的公演引起了轰动,又一次,《日出》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权威人物的批评,这一次是周扬。他在《论〈雷雨〉和〈日出〉》一文中指出曹禺的作品“现实主义不彻底、不充分”,“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力量在《日出》里面没有登场。”
这一次,曹禺保持了沉默。
蜕变
全面抗战爆发后的8月7日,曹禺的第三部大戏《原野》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隆重推出。与前两部作品的轰动截然相反,这部讲述农民复仇故事的作品没有几个观众。而同一天,上海蓬莱大戏院上演的抗战话剧《保卫卢沟桥》,却盛况空前,剧场上下响彻救亡图存的口号。
1938年6月,曹禺在一个“战时戏剧讲座”上发表演讲:“一切剧本全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,不单是抗战剧……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,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”。这与他当年对《雷雨》的阐述相比,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。
1938年10月,重庆第一届戏剧节开幕。由曹禺、宋之的合编的话剧《全民总动员》作为压轴大戏,在国泰大戏院公演。这是一部为国共合作抗战主题专门订制的作品,描写了一群爱国青年同日本特务“黑字二十八”的斗争。由于“政治正确”,这部戏公演后得到了国共官方媒体的一致肯定。也就是从该剧开始,政府官员的形象首次出现在了曹禺的作品中。1940年,他又写了另一部旨在反映民族抗战中“蜕旧变新”气象的话剧《蜕变》。
然而,40年后,曹禺在家中对王蒙语出惊人:“从写完《蜕变》,我已经枯竭了!”
事实上,此时的曹禺,有着很多灵性和情感,无处挥洒。
1940年,曹禺在江安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方瑞。随着爱情的到来,曹禺也又一次燃起了塑造“人”的激情。在同年创作的《北京人》中,他用“全副的力量”,以方瑞为原型创作了“愫方”这个主要形象。对于这部作品,曹禺回忆道:“我倾心追求的是把人的灵魂、人的心理、人的内心隐秘、内心世界的细微的感情写出来。”曹禺的女儿万方谈到《北京人》时则充满了钦佩,认为父亲“在抗战的时候,并没有忘掉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”。
1941年10月24日,《北京人》由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抗建礼堂上演,由于“连日观众拥挤”,一直上演到了11月8日。1942年1月,中央青年剧社再次公演《北京人》,依然延续了轰动效应。茅盾在一篇剧评中认为“作者又回到从来一贯的作风。这是可喜的”,不过他马上又问道,剧中的袁氏父女,“他们的思想意识,在我们这个社会里,相当于哪一类人?”而一些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,左翼作家胡风认为“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,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”,杨晦直接把《北京人》称为曹禺创作道路上的“退转”,认为它是在给封建道德和封建情感唱挽歌。
对于这些评论,曹禺仍然保持了缄默。
转型历史剧无果,1944年,曹禺的目光又回到了现代剧。他看了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后,认为“应当去写工人农民”,准备写一部工业题材话剧《桥》。不过,这部戏最终只发表了两幕,因为抗战一结束,曹禺又接到了一份新的工作——应美国国务院邀请,和老舍一起作为文化使者前往美国讲学。
此时是1946年1月,内战的阴云已经渐渐笼罩,每个人都将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。
选择
据曹禺回忆,1938年初,他随剧专迁到重庆后,时任国民政府教务部政务次长的顾毓前来拜访。然而,当顾毓拿出一份国民党的入党申请表时,曹禺却当场翻脸,斥道“你拿这个干什么?”弄得顾毓尴尬万分,怏怏而去。
还有一次,剧专校长余上沅邀请曹禺到家中吃饭,席间余上沅的夫人陈衡粹问曹禺:“你怎么这么喜欢共产党?”曹禺反问: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共产党?”
1937年曹禺见到共产党元老徐特立,对徐的印象非常好,因为在他眼中,徐特立和他的小卫兵尽管是上下级,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。后来,在抗战话剧《蜕变》里,曹禺还以徐特立为原型,塑造了一个恪尽职守、一身正气的视察专员“梁公仰”。“以后我认识了周总理,是1938年在重庆见到的,谈得就比较深了。”曹禺还回忆道,“那个时候,只要是去曾家岩,走起路来就脚下生风,心里头也畅快极了。”
“周恩来对他的戏是非常欣赏的,在重庆的时候就看过他的戏,后来解放以后,北京人艺演出的时候周恩来常常去看,而且演完以后到后台跟演员聊天。”万方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说。
1945年秋,在周恩来的安排下,曹禺见到了前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:“足下春秋鼎盛,好自为之。”一同参加会见的知名人士只有二十几人。
1946年1月,曹禺接到了赴美国讲学的邀请。“我当时拿不定主意,到那里该讲些什么呢?”,曹禺决定找人请教——他把电话打给了八路军办事处。由于吴玉章、董必武等人均不在,曹禺又去请教茅盾。茅盾告诉他,“要讲文学是有社会意义的,不只是娱乐”。果然,在美国期间的一次聚会上,曹禺阐述“文学的社会意义”后,与强调“趣味主义”的林语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,两人不欢而散。
1946年7月15日,闻一多在昆明发表了“最后一次演讲”后,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。同闻一多素有交往的曹禺极为震惊,“对国民党的残忍痛恨到极点了。”1947年1月,曹禺提前结束了美国之行。“从美国回来后,和共产党接触多了,对党的信心加强了。那时,我的想法是:恐怕唯一的出路就是共产党了。”
1949年1月,北平解放。2月,曹禺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由上海转道香港,前往北平参加正在筹备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。临走前,他对黄佐临说:“世道要变的,将来是大有可为的。”
怀着“大有可为”的理想,曹禺又一次踏上前途未卜的旅程。
梦醒
新时代的到来,让曹禺充满了激情。在抵达北平后的几个月间,曹禺陆续当选为第一届文代会常务委员,全国剧协常务委员,全国政协委员。用他的话说,“一种翻身感油然而生”。
同时,曹禺被赋予的工作也陡然增多。据万方讲述,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曹禺负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,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华演出时,“每一场演出中间他到整个舞台上去看一遍,看见哪有一个小钉子出来一点,赶快让舞美的人把这个钉子给敲进去。”而据1954年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梁秉回忆,当时身为人艺院长的曹禺甚至曾经一天去接五次飞机,繁重的事务工作之余,他有时只能向剧院的“小字辈”们打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“我哪里懂得这些事?凭了一股热情,叫干啥就干啥,以为这样做就是我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。”曹禺晚年说道。
1950年10月,曹禺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》。他自我剖析道:“我是一个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”,“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X光线中照一照,才可以逐渐使我明了我的创作思想上的脓疮是从什么地方溃发的。”
很快,他开始对他的“脓疮”动手术了。
1951年,曹禺应开明书店之约,编辑《曹禺选集》。借此机会,他主动对自己的三部代表作——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进行了删改。
不过,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《曹禺剧本选》时,曹禺又恢复了三部作品的原貌。“现在看,还是保存原来的面貌好一些。”曹禺在前言中说道。轻描淡写的一句话,背后蕴藏的矛盾心境,耐人寻味。
一个月后,曹禺开始试写新生活了,他要写《明朗的天》。
早在1952年,曹禺就开始着手准备这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,他以协和医学院为蹲点单位,用了三个月的时间,参加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,做的笔记甚至达到二十本之多。
在1953年第二届文代会上,曹禺这样诉说道:“四年来,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,我经过土地改革、文艺整风、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,但是我还没有写出一点东西。应该说,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。”
然而,1954年4月《明朗的天》动笔后,曹禺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艰苦。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谈道:“尽管当时我很吃力,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,是硬着头皮去写的,但现在看来,是相当被动的……”
“他有一句名言:不真知道,不深有所感,就不能写。”梁秉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说。
《明朗的天》和后来《胆剑篇》、《王昭君》,这三部为宣传而作的戏,成为曹禺建国后仅有的话剧作品,它们都再也没有重现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的辉煌。
1980年,曹禺接受采访时,说出了长久以来的思考:“我们总是写出那些‘合槽’的东西,‘合’一定政治概念的‘槽’,……真正深刻的作品,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”,“不要把人性看得那么窄小,不要用政治把人性扣住。”这些思索,与1935年他对《雷雨》的阐释,如出一辙。
只不过此时的曹禺,已经找不回当年的状态了。他没有再写出新作。
1996年12月13日,曹禺病逝。
此前,曹禺夫人李玉茹已经为他在万安公墓做好了墓地,请他看。曹禺看到墓地周边有铁链围着,说:“不要围起来,要开放些!”